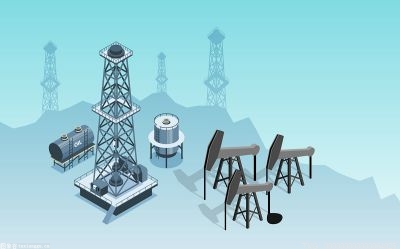文 | 李东平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小麦返青时节,想起那些年的麦收…...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我家住在汶河岸边,闻名古今汶阳田就指我们这儿。每年五月底,一阵干热风吹过,金黄的麦浪如仙女织就的地毯,平铺在汶口大地,这时收麦子就开始了。
小时候印象麦收,是隆隆的崂山机子的山吼,仿佛一进了这个季节,潜意识就会耳畔有这回响。那个叫“臭耷翅子”的小鸟开始叽叽地站在枣树枝头唱响。娘说这种鸟长得好看,但千万别逮,它会放臭屁,屙屎。我却喜欢它头长着皇冠,羽毛红白相间像啄木鸟似的。
这时,爹会在歪脖枣树下吱呀吱牙,使劲磨着生锈镰刀,一条长长磨刀石经过多年的磨练,磨成了月牙形。爹磨完镰刀后找个玉米皮的铺墩坐在上面,把镰刀放在破旧布鞋底上来回蹭,爹说这叫铛刀,使起来耐用。一早晨爹就这样除了磨就是铛。磨刀不误砍柴工,可能有一定道理。
吃罢早饭,母亲罐满一泥瓦罐的绿豆水,有时也有大米水,爹拉着用木棍扎裹四周的地排车,娘领着我们姊妹四个,留小妹在家烧水,一直到西坡五亩三去了。我家地块我是熟悉的有十五亩,六亩四,五亩三,都是一种代称,我最喜欢这个紧邻南西遥村庄的五亩三,又短又好割,还紧邻两村石渠,累了渴了,往石渠上石头条子上一坐,又解渴又凉快,还可以看许多花蝴蝶在七菜花上飞。
娘说我要饭牵着猴子,玩心不退。凭我十四年龄,一尺八的小腰过秤也就七八十斤,能出坡干活己经不错了。人说“人长十岁不吃闲饭”。像我这年纪有的人家当整劳力使了。
爹娘种着八口人地,有两亩大地,迫不得已才会让我们这些孩儿下坡的。眼看着天边云头,上来又下去。爹在手里吐口唾沫,一声不响开了第一镰,随后,娘在腰上系好麦秸药子(绳),腰儿一弯,镰刀划过一道美丽弧线,一截麦穗齐刷刷被娘割下来,那动作又干净又利索,对于四十刚出头母亲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她边干边回头示意我们:各人选一畦,早干完早歇息。
爹娘种着八口人地,有两亩大地,迫不得已才会让我们这些孩儿下坡的。眼看着天边云头,上来又下去。爹在手里吐口唾沫,一声不响开了第一镰,随后,娘在腰上系好麦秸药子(绳),腰儿一弯,镰刀划过一道美丽弧线,一截麦穗齐刷刷被娘割下来,那动作又干净又利索,对于四十刚出头母亲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她边干边回头示意我们:各人选一畦,早干完早歇息。
我自然占住了苗稀断垄一畦麦子极不情愿地半弯腰搭上镰,吃拉,一撅麦子像波浪似被我请到手中,又像天女散花似的扔到身后。我一边干着还一边看看身旁大姐三姐,只见她们生疏地虾下腰,吃力地割着麦,小心翼翼又仿照父母把麦穗一堆一堆排在身后。这样无形中影响了她们进度。我吃吃笑她们愚。
我一边割麦一边抬起脸四下张望,只听的头顶上飞过一架飞机,那是东山上军机正在演练呢。
娘在前面边割边喊,″小四,别光看了,割麦要紧!"
我答应着弯腰却看到一根大蚯蚓爬上脚面,"长虫(蛇),长虫″。我连咋呼带喊跳将起来。原来是我不小心拉起一兜麦,连土带蚯蚓的一起请出来。
爹跑过来,娘又一阵骂。我总是这么不省心也总是慢腾腾地干到最后。
休息时娘宣布一个命令,谁割的麦子谁自己捆。我回头看看狼趴窝的功绩,人直接就卧到了,还是爹替我打扫战场才算装满车,拉到麦场去了。
眼看中午的太阳如同一面耀眼明镜,炙烤着炎热大地。大中午头里终于等来十岁妹妹,一手提壶,一手用笼布包来干粮,家里有早上母亲煮的咸鸡蛋,再加上自留地里摘的黄瓜,小葱,一顿不算丰盛的午餐在地头上开始了。我瞅瞅远处二大爷家三个小子,一人抱着半块大西瓜,坐在大柳树井沿上,像柳树上知了叫的那么烦人。
利用这会功夫,大姐她们半躺在麦垛上,一会儿就吃啊喝地睡着了。我愁容满面地望着麦地,叨着一棵狗尾草说啥也睡不着。爹继续磨着他的镰刀。
"轰隆″一声炸雷,天际间上来一块大黑云,劈呖啪拉的斗大雨点落在人的热脸上。大雨一下来到头顶上了。
只见大风刮动麦田就像大海掀起巨浪,人们头上帽子,身上衣服都被吹起老高。
这时娘想了起来似的喊了一声,"快上场,那儿还晒着麦呢。″
爹拉起半车麦捆就跑。我们几个也像脚踩上风火轮。只见老远就看哪晒场上,老的老少的少,拿掀的拿掀,挥扫帚的挥扫帚,就像千军万马般沸腾跳跃着,大家齐心合力抢收着到嘴的果实……
这时太阳像与人开了天大玩笑,猛然泻下一地银光,天晴了,风住了,我们也累瘫了。
【秋枫荐语】李老师的文章,充满着浓浓的家乡气息及感情,暖暖的欢乐回忆及美好、吃苦的童年。
作者简介:李东平,女,70后,泰安市 岱岳区大汶口南西遥人。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发表于各媒体网络,“泰山文化”“中国诗歌网”“汶水之滨”等。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