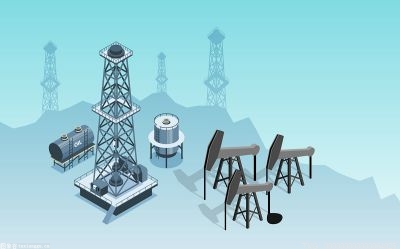正文之前,最好先看完《穿越》全篇和《谎》,并从第一篇开始看,以保证内容的连贯性。创作不易,点个赞吧!
苏醒第一年 7月27日
上天总会在人间降下很多特别幸运或不幸的人,我大概是其中不幸的那些之一。尽管政府已经将量产休眠舱对人体的损伤率降到了最低,也还是会有在休眠时出意外的案例,比如我。相比那些肢体局部坏死的人,我或许是最幸运而又不幸的,因为我的症状是失忆。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神经科病房的人很少,但也都很奇怪。别的真是有精神疾病的我能理解,但更多的人都是装的,一天时间就架出去五个,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害怕,毕竟他们要是觉得我在装怎么办?不过至少今天我还没被赶出去,希望在我恢复记忆前一直如此。因为人少,所以我被分配到了一间双人病房而非走廊上,病友是个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的男人,但他说话的风格总感觉......有点奇怪。他不肯说自己是患了什么病,不,他是一直在说自己没病,但进出的护士没有一个理他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肯说,只是固执地重复自己没病,再过一会儿就能走了。
我问他的名字,他起初不肯说,只是一直小声嘟囔着些我听不太清的话。后来,他的态度忽然变好了很多,过来主动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失忆了,不记得,他显得很惊讶,却还隐约有点像......惊喜?他说每个休眠舱上应该有名字等身份信息,让我去问问送我进来的护士。我原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当时被送进来时没问,于是我按下了呼叫铃。
他现在忽然肯自我介绍了,而且他刚才那种奇怪的说话风格也变了,我忽然觉得他好像是应该待在这里的精神病人。他说他叫zheng,我问他哪个字,他不肯说,还让我别问护士,他说他不想听到他最开始的名字。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虽然我的确怀疑这名字是他编的,但他既然想让别人这么叫他,我也就在我目前有限的文字储备中找一个适合做名字的字:郑。
和郑聊天一般是令人愉快的,他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对于我的问题也耐心地尽数回答。苏醒时,我只记得我是因为某些原因休眠了,休眠之前发生了什么完全不记得,我的失忆是休眠导致的这件事都是通过报纸猜测的,但病房读报栏里的报纸太少了,上面又充斥着各种商业广告,所以我觉得还是问人方便一点。
郑是前一天苏醒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知道得很多,只是在他回答的时候常常忽然停一下,好像嘴里还念念有词,鉴于他可能患有的某些疾病,我不好多问。他说人类是因为一颗闯入太阳系的小天体才被迫大规模休眠的,这颗天体在太阳和木星等巨行星的共同作用下,轨道很复杂,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球表面会降下大量原本由那个小天体(它被命名为“灰烬”)携带的尘埃,甚至可能还有部分从小行星带受影响变轨的小行星。最重要的是,“灰烬”上有一种未知物质,当时没有人见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推测出来的,说如果太阳受到这种物质的作用可能会触发严重的爆发。一开始肯定引发了舆论的集体嘲讽,但后来越来越多的政府也开始支持这种说法,最后,全球都开始为长期避难做准备。这样才有了休眠计划。
计划分为两个部分:地下城和休眠舱。“地下城”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更像一个仓库,用来存储休眠舱。本来更受支持的是生态循环系统计划,但后来,一个组织忽然一炮打响,指出它们已经在休眠舱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并认为各国政府应考虑当下的实际情况。郑好像知道什么内情,他告诉我,当时大部分政府其实都没有能力在预测中第一批尘埃到达之前完成地下城的开掘并同时完成生态系统的研发,如果真这么下去,第一批尘埃到达之前完成地下城的开掘并同时完成生态系统的研发,如果真这么下去,第一批尘埃能掩埋全球约五分之三的人口。各国都心照不宣地没有公布这个消息,要是没有那个组织跳出来,还不知道后来要发生什么,甚至有人怀疑那个组织其实就是某些国家秘密进行的研究的研发团队。
最后,除了少部分不愿搬迁敢于直面死亡的人留在地表,各国轮值元首、自卫军、维持休眠舱运作顺便观测“灰烬”的科学家们,全球的人口都进入了休眠。自文明开始发展以来,地球上很少有如此安静的时候。
现在,“灰烬”被木星的引力捕获,成了木星最大的卫星,已经有配备最新装备的无人飞船去探测它了。所有休眠者正在分期苏醒,重新建设地上的基础设施,并修复仍然可以使用的部分。我和郑是因为疾病才能在医院一直待着,其他人都要上地表去工作。
我问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他说他又没有失忆,之前的事情他本来就知道。我知道自己犯傻了,打了个哈哈。我问郑的年龄,他说去掉休眠期间已经二十七岁了,他是公元二十一世纪初出生的,被称为“末代人”,比他们出生晚一点的叫“新代人”,现在还没苏醒,划分界限是休眠时是否满十八岁。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问我大概多少岁,郑沉默了一下,然后又开始喃喃自语,接着才回答我说大约十八九,我才意识到我离“新代人”只差一步之遥。
我们住在地下城的医院,并没有昼夜之分,但医院有熄灯时间,郑看起来也累了,我就主动提出睡觉。毕竟我才醒来一天,很多东西还是慢慢来比较舒服。
7月28日
今天一早起来就发现郑不在他的床上,我以为他在上厕所,但锁着的门里却传出争吵的声音,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但能觉察到这是争吵,而且双方的声音似乎很像。我看了眼时间,发现自己睡了大约十个小时,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困倦,我想起昨夜的一个噩梦,或者说,那不是一个梦。那时我忽然从床上醒来,看见郑没有睡,而是在床上坐着,口中念念有词。我听不太清他在说什么,因此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梦中,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只是又昏昏沉沉地闭上眼,竟然真的就这么睡着了。不过房间里一直有一盏夜灯开着,我总感觉那时郑也看到了我睁眼,所以早上起来我本想好好问他一下的。
没过多久,厕所的门开了,郑走出来,脸上满是阴云,但他一看到我,就又恢复了昨天那样的笑容,问我睡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我一边答着一边犹豫该不该说昨晚的事,郑却没有回自己的床上,而是做到我身边。他仍然在笑,但说出的话却让我不禁浑身打颤:“你相信人死后都会去往什么地方和亲人见面吗?”我很吃惊,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想干什么。
我当时应该是回答了什么,但我记不清。因为郑又问了一句:“要不,你帮我试一下?”我真的害怕了,伸手想去按床头的呼叫铃,然后就忽然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清醒过来时,一份早餐已经放在我的床头柜上,郑坐在他的床上吃早餐,脸上仍然挂着笑。见我醒了,他说:“怎么才醒啊?都八点多了,早餐我帮你拿了。”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又吃惊又害怕,可能还有疑惑。见我不回答,郑又说道:“怎么?想起你休眠前的事了?”我十分确定他之前已经问过我类似的话了,但想起他早上的表现,和眼前这个人截然不同。这不会又是个梦吧?我试探着问了一句:“你今天几点起的?”郑的表情毫无波澜:“六点左右吧,以前上学的时候习惯早起了,休眠之后也没改过来。只是现在早起的确挺无聊的,休眠之前的游戏现在都暂停开放服务器,只有单机可以玩,之前那些视频网站和软件更是用不了。不过应该也就我们前面几批人无聊一点,等后面人多了,上面的建设差不多了,应该就能好些了。”
直到他说完,我才忽然发现我的记忆有很多都处于一个似有似无的状态,他提及的这些名词我都有印象,但却又想不起来有哪些游戏,哪些软件。但我当时关心的不是那些,而是我方才脑海里的那些记忆,究竟是不是一场梦?
“我从早上到现在,中间一直没醒过吗?”我决定问得再大胆一点,得到的却是令我有点失望的回答:“没有啊,我都能听到你打呼噜。你做噩梦了?”失望过后是轻松,其实那点失望都不应该出现:谁希望自己的室友犯起病来这么严重呢?但接下来的一天我还是可以和郑保持了距离,并趁一次单独见护士的时候上报了这件事,毕竟我们都住在神经科,万一郑真的是精神分裂呢?我得预防一下。
今天从护士的谈话中听到,失忆其实是症状最难检验,但后果并不严重的病。即使真的确诊且治疗无效也能出院工作,开张证明就行。所以说,我现在更像是出于“度假”状态,甚至还可能有找回记忆的意外收获。昨天对我进行的都是检查而非治疗,毕竟伪装失忆的人很多,一上来就开药容易让他们得逞,再加上正值苏醒高峰期,所以今天我也只有寥寥几项检查项目,而关于我是否真的在梦中看到了郑发病,可能要明天才知道。
如果没有今早那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郑这个人其实还挺好相处的,除了他偶尔会自言自语之外,他都称得上一个好室友。今天一早护士就送来了我们休眠前寄存的私人物品,虽然我忘了隐私密码,但还有很多种生物特征比如指纹可以开锁。里面的东西令我有点失望,因为他们没能引发我的回忆,不过它们本身承载的信息还有点小用。我只留下了一些书和手机,以及手机的各种配套设施。郑在知道后很兴奋,在我给手机充电时一直在我边上守着。开机以后,在郑的建议下我用生日打开了手机,我意外地发现刚才郑提到的软件中有好多都在手机里。郑激动了一下,但很快又变成失望,然后就到一边去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好不容易有与他存在共同语言的人,可我却不记得这共同语言中的任何内容。
我翻看了所有我曾经的聊天记录,但刚开始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的家人在哪里?郑说他也问过医院,得到的答案是有一个区域的地下城发生过坍塌,好巧不巧就损坏了集成储存单元。大部分信息都有备份,但因为休眠前计算机的性能问题,仍有部分信息没有备份,比如亲缘关系,必须苏醒后运气够好才能亲人相认,且苏醒是分批次和年龄的,即除了我们的同辈人,别人都还没苏醒。
通过手机,我得知我和郑一样是独生子,名字叫刘传,父母都还健在,但再上一辈的老人都在休眠前去世了。我还有几个朋友,但我完全不记得,也不太想去麻烦他们。后来和郑聊这些事的时候还有个意外收获:我们是同乡。现在“同乡”已经不指籍贯相同,而是指休眠前的居住地。他还正好是我上的那所中学的学长。哦,忘了一点:我今年十八岁,休眠前好像正在准备参加什么考试。郑说那叫高考,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这让我再次对自己的记忆缺失很疑惑,为什么它们缺失得......毫无规律?我对现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没有任何概念,只能希望记忆的缺失不要让以后的生活太艰难。
做完检查以后,郑问我什么时候出院,他想和我一起走。我说不清楚,又反问他怎么能控制自己的出院时间。他只是笑笑,让我就当这只是他的一个希望。我一开始怀疑这话是不是说明他在装病,但又想到他昨天极力声称自己没病的样子,这个念头很快打消了。
注:文件已按首字分类法储存于文本库中,查收通路正常。保存:完成;备份:完成。文件信息已确认;文件已挂起至发信栏。后续正常文件均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