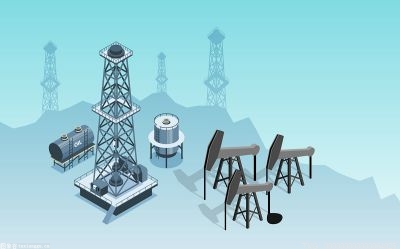孔令麒和程蔓吵架了,堪称他们结婚之后的破天荒历史大事件。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秋去冬来的又一次启航例行酒会上,有人看到她和聂峰还有杜一鸣笑谈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回复当时还在国外出差,顶着水土不服的难受征求她伴手礼意见的孔令麒信息。
更要命的是,她在散场出门时扭到了脚,是聂峰把她抱上车去的医院。
一个冒着大雪冻成丧尸还能踩着高跟鞋爬山的女超人,能在这种工作场合肆意欢笑和意外踩空,还不避讳地让其他男人公主抱自己仅着晚礼裙的身体,现场的人怎么想不知道,反正当时在酒店吐到天旋地转的孔令麒是接受不了。
那些内部群里传播的视频和言论,让他病了几天的精神状态愈加糟糕。
第二天早上扔在一边的手机响起了程蔓专属的来电闹铃,他也没有心情接。
比起当初没有设备跑路的心虚,此时的他更多是醋劲未消的烦躁。
微信和电话铃声交替灌入耳中,他气得干脆把脑袋塞进了枕头底下。
推门进来的黄毛傻眼了。
“哥,你咋还不起来,都到赶飞机的点了!”
“不想去了,帮我改签,我要睡觉!”
“你手机响着呢……”
“别管那么多,出去!”
看着折腾一地的衣服和一团糟的床上,懵圈的黄毛也不敢多问,只好带上门转身离开。
坚持不懈的手机终于安静下来,被窝里断断续续的呜咽声又打破了屋里的沉寂。
换了平底鞋的程蔓在深夜的寒风中站了好久,才看见推着两个行李箱的黄毛从通道出来。
双手插兜的孔令麒独自走在后面,板着的脸上阴沉无神,通红的鼻尖下还挂有清水。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嫂子久等了吧?”
“还行,我就刚到。快上车暖和一下……”
她上前挎过孔令麒的胳膊,抹了一把他湿漉漉的鼻子。
“又感冒了?”
他嘴角动了动,却没有回答,扫了一眼她关切的眼神,也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声。
闭目抱着双臂靠在后座上的他一言不发,大概是被她来回擦鼻涕的纸巾磨痛了皮肤,干脆侧过身去缩着,留下她面对一个黑漆漆的背影在发愣。
见车里气氛不对,黄毛赶紧打圆场。
“嫂子,他水土不服几天了,今早还起不来,这才改签的……”
“水土不服?他没跟我说啊……”
“可能怕你担心吧,他也不让我说……”
望着他不再动唤的身子,她也不问了,轻轻给他拉好蹭歪的毛线帽檐,转而悄悄活动了一下还有点刺痛的脚腕。
车窗外掠过的霓虹灯,照在他呆滞的双眸中,晶莹的泪花滚落出了泛红的眼眶。
到家已接近凌晨,瘫坐在沙发上的孔令麒,扒拉下帽子甩到角落。
久未认真进食的肠胃仍在隐隐作痛,然而嗅到程蔓端过来的甜粥,还是没有张口的欲望。
“怎么了,还是不舒服吗?”
“你的脚怎么样了?”
半天才憋出一句话的他,无精打采地看着眼前人。
“没事,就是崴了一下。那天是地上滑才出的意外,没伤到骨头,过几天就好了。”
“既然没事,为什么他抱你那么自然,你也没有拒绝呢?”
她的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脸上。
“什么意思?”
“你们群里不是都传疯了?”
“那些人就远远偷拍一下,了解前因后果吗?你直接信他们说的?”
这些流言蜚语她一向不爱沉迷其中,但是重新翻着聊天记录,看着那晚不同角度和距离的路透,有的甚至还专门推镜头放大了局部特写,再配上各种内涵意味的画外音,很难让人不浮想联翩。
尤其是部分画面,聂峰的手是穿过裙子的布料直接抱着自己的,下摆开叉的地方也有盖住了他的指头,加上她下意识挽着他的脖子,即使当事人再无意,旁观者也没法选择性忽略。
看到他那晚很早就发来的伴手礼样品照片和录像,还有叮嘱她少喝酒多保暖的话,可惜她都没顾得上瞧,就被铺天盖地的满屏群消息给刷没了。
现在要想解释什么,恐怕得好好琢磨一下了。
“我和他们两个从头到尾都是在谈工作,而且是对多比目前发展形势大好的肯定。”
“至于扭到脚,就是个意外。我说要自己走,他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行动了。我是担心摔下来才没有马上回绝,他一送我上车就什么都结束了。”
“你不是说,自己从来都不相信意外的吗?”
“那是事出有因,我这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孔令麒不吭声了。
望着他和那晚遭到黄毛背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哀怨神情,委屈的程蔓瞬间不知道该从哪为自己辩护起。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
“不用说了,我还能不信吗?你的脚没事就行了。今天去接机也累了,早点睡吧。”
这话听着比刚才郊外的冷风还要低上几度,她也没有争下去的劲头了,气冲冲地直接站起来。
受伤的脚险些没立住晃了一下身子,腰后被他条件反射地扶到。
但她只原地停了一秒,抓过茶几上的碗摁进他没来得及收回的手里,丢下一句“赶紧吃完去洗漱”,便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
目送着她消失在楼梯尽头的身影,断了线的豆大泪珠沉入了毫无波澜的粥面。
他还是握起和手指同样颤抖的小勺,把渐凉发苦的夜宵一口口填进了绷紧的喉咙。
心事重重的程蔓一大早醒来,发现身边的位置空空荡荡。
床头柜上搁着包装精美的礼物,还压了一张纸条。
“姐,我出去散散心,午饭不回来吃了。”
大周末的,这是又闹哪样?
她急忙打开手机,居然没有一条来自他的未读信息,微信拨过去也不接,改打电话竟然只有语音信箱。
“姐,我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别担心,有事留言就行。”
掀开被子跳下来的她探头到浴室一看,里面干燥得几乎没有水汽。
楼下的餐厅还留有新带回来的糕点,就是没有他的影子。
睡懒觉起来的田爽完全还在状态之外,她又不好直接告诉实情,只能随便应付了一下。
吃完早餐到车库一看,地面从昨晚就保持纹丝未动的车辙,令她深感不妙。
他到底跑哪去了?
午饭时间过后,就差在朋友圈发寻人启事的程蔓也不想找了,独自窝在床上生起了闷气。
不就是晚了点照顾他吗,自己什么人他还不清楚,有必要这样耍脾气?
定位也失灵了,累得晕头转向的她干脆搁下手机,拉过被子睡起了午觉。
下午郊区的墓园里,阴沉沉的天空让原本就冷的空气凝成了冰坨。
一方擦得光洁如新的墓碑上,嵌着的照片是一位秀气漂亮的女人。
旁边成束的菊花微微扇动着淡黄的薄翼,甬道上却摆着一盆还挂有露水的郁金香。
通身黑色装扮的孔令麒,提着一小瓶白酒和三个酒盅缓缓走了过来。
他盘腿坐下,将一字排开的杯里逐个斟上了大半。
端起最中间的杯子,在碑沿轻轻碰了一下。
“妈,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就是突然想你了,过来看看。这段时间你怎么样了,有没有惦记我?”
把淅淅沥沥的酒洒落在草缝里,他改换了左边的新杯。
“这几天发生的事说多也多,其实也不能算是个事,你说我干嘛就非要和程蔓过不去呢?她对我的心可是经得起考验的啊……”
握着杯子的手想和右边的也碰一个,低头想了想,还是放弃了,自己仰脖一口饮尽。
“妈,姐,我这人啊,容易受别人影响,这毛病暂时还改不了。”
“这次呢,主要还是我挺害怕历史重演在自己身上。要知道水土不服的每一秒,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倒在外面回不来了……”
“没夸张,好几次眼前都是黑的,你看我现在有没有瘦一点?”
“妈,我能体会到你当初生病时的感受了,很难、很脆弱,身边只有一个徒劳添乱的傻小子跟着。不光是身体上痛苦,精神上也会崩溃……”
“姐,你能原谅我的不懂事吗?我确实不该在你受伤了还胡乱猜疑,只是心里有道坎,我至今还没有勇气迈过去,也没想好要怎么和你说……”
他抚着面前郁金香的花瓣,两手交替着把杯子在盆边陆续触下。
“再等等吧,最快今晚才能给你答复了。我实在太笨了,说不清楚又会惹你生气……”
一前一后灌下两大口,辣得发晕的脑瓜子嗡嗡响。
他心一横,干脆抄起瓶中剩下的酒全部倒进了嘴里,任凭胃部喷涌而出的热流像山火一样燃遍全身。
过了片刻,他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朝墓碑深深鞠了一躬,伸手搬过花盆搂在怀里,迷迷糊糊地走了。
夜深了,程蔓还驾着车在沿街寻找。
她把上海能想到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搜遍了,游戏厅、夜店、酒吧,包括日常去的几个咖啡馆和餐厅,嘴皮子都磨破了,但是没有就是没有。
又怕他想不开,她顶着外滩猛烈的江风,拼命识别本就没几个人影的面孔。
脚下的路在时断时续的阵痛中似乎一直没有尽头,她一开始还冲空旷的四周呼喊几声,可都在风里渐渐吞没。
偶尔在长椅上歇会,活动活动麻木的手和酸疼的腿,稍微缓过来后掏出手机看看情况,又继续踽踽独行。
她忽然觉得自己能体会到他那几天独自在外承受的煎熬了。
自小在上海长大的他,尽管推崇非素食主义,但也没养成口味偏重的程度。
特别是到东北那段时间,被各种酒围攻得连出了几次洋相后,回来也逐渐和这些杯中物划清了界限。
除了一些特殊的重要场合,他没再贪恋于酒精的自我麻痹中。
连续几天的水土不服,肯定是被折腾得内外俱伤,但是多比的业务和自己的礼物都没落下,付出的毅力绝对不小。
这次也的确不能全怪他过分敏感,自己在他乡孤立无援,唯一心爱的人却不闻不问,何况还多了这么一出内涵不明的破事,其中肯定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实在走不动了,找了个僻静角落的凉亭,靠在冰冷的柱子上,裹着身上存在感似无的羽绒服缩成一团。
风声越来越响,黄浦江面掀起了滔滔巨浪,两岸不灭的流光溢彩揉碎成朦胧的烛火,绵延在通往遥远梦境的天际,又一点点摇曳着熄去。
程蔓在眩晕中昏昏沉沉地醒来时,一层薄薄的纱布替她遮住了双眼,揭开后发现自己正躺在亮着柔和灯光的病房里。
床边趴着守夜的,居然是那个让自己担心了一天的孔令麒。
“孔令麒,孔令麒?”
连推了好几次,他始终没反应,倒是一股还没散去的酒气吓了她一跳。
他这是又去喝酒了?
看看手背上扎着的针,仍然迷糊的大脑告诉她,自己发烧了。
难道是昨晚受凉过度的自己被他找到送过来的吗?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哪呢?
挠着神智混乱的脑袋拼命回忆,昨晚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重新浮现在她眼前。
周末的外滩夜生活繁华依旧,灯火通明的店铺里外人头攒动,进进出出的外卖员脚不沾地。
一家烟火缭绕的大排档里,与那盆郁金香对坐着的孔令麒,沉浸在孜然与肉香的世界中大快朵颐。
郁金香前面桌上的小盘里,也摆着新鲜出炉的玉米、茄子、土豆、牛肉等,均是外焦里嫩的良好卖相,在保鲜膜的覆盖下渗出热乎乎的水汽。
饮下一口啤酒,擦了擦嘴上的油渍,他整理了仅剩的一点烤串,瞥见架在花旁等候录制的手机,有点紧张地拨弄着沾上烟尘的帽顶。
“姐,还记得我第一次向你敞开心扉的那个夜晚吗?你问我喜不喜欢你,我说喜欢,非常喜欢,但不知道是不是爱,即使当时满脑子都是你……”
“这就是那天提到的前一晚梦见我俩一起吃大排档的地方。也许是铁锅炖留下的初吻暴击,让我想象起了如果是在上海的同样场景,又会是个怎样的剧情?”
“说实话,我目睹了父母多年折损在吵吵闹闹的所谓感情,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过自己对他们的意义何在。”
“我妈为了我能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里,忍辱负重到久病离开。她早就知道我爸变脸的根源了,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可这样又能换来什么呢?掏心掏肺的卑微,到头来还是被当成负担踢进了墙角。”
“我呢,对事业一向都是全身心投入,说是和这些谈恋爱也不为过,毕竟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念头去一手打造成梦想的模样。”
“只可惜,天意不为我生,我的赛车俱乐部散了,游戏公司吹了,人工智能被抢了,仅尝试着开始就草草收尾的两段爱情也不会经营,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不配和成功沾上边,多比现在是在想方设法给用户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可我连维持住自个小窝的底气都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不相信过你,只是聂峰和其他人那晚的言行,不管他有没有意思,都在时刻激起我内心深处最恐惧的那份担忧。”
“作为糟糠之妻,我妈也没挽回财迷心窍的我爸;他骂走了我的初恋,用钱买断我的未婚妻,还妄图拆散现在的我们。资本和舆论真的是当下两道配合默契又根基牢固的铁腕,一旦联手,天真善良都只能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也不想看见托付终身的人是这样一副怯懦的样子,但论资质谈吐和了解,别说是聂峰,圈里能秒我的人一抓一大把。”
“我至今还记得我妈对我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那一晚,她哭肿了眼睛,却什么都不说,从此她也不再避着我发脾气,反而看见我非骂即赶,情绪不定得随时可能发疯。”
“她只知道自己给过我爸做过好吃的家常饭,生过一个还算可爱的儿子,却不知道这些小事在他眼里早就一文不值了……”
面前盘里的泪水汇聚得越来越多,把肉块上糊着的果酱都泡化了。
进来收拾桌子的老板诧异地看着哭成狗的他朝一盆花在自言自语,忍不住凑过来问:
“孔少,今晚这是怎么了?和媳妇吵架了?”
“没有……”
“我那还多烤了两串腰子,要不要带回去?”
“不要!你留给自己吃吧……”
老板无奈地摇摇头走开了。
他静下来消化了一下情绪,扯过纸巾胡乱划拉着脸上的痕迹,强打精神沙哑地喊了一句。
“老板,买单!这些没动过的打包带走……”
锁好手机的他又一次恍恍惚惚地扶桌站起,弯腰捧过花盆后小心翼翼地装进背包,接过老板递上的外卖盒,晃晃悠悠地踱入了迷离的灯影之中。
外滩的风依然吹得人耳鸣心跳,也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空气和江中肆意搅拌。
孔令麒一米八几的身子在反复横扫的寒风中打着醉拳,通红的脸不知道是酒劲上来了,还是风划的,眯成一条缝的双眼沾满了尘土。
不知不觉他也踏上了台阶,摘下背包直接躺平在一条凳子上冒起了汽笛。
斜对面另一个模糊的人影动弹了一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
他抬眼瞧去,手提包表面上反光的logo,就是家里常见的印迹。
再拼命睁开打架的眼皮仔细一看,这发型衣服和鞋子的一系列组合,已经实锤了。
“姐,姐……”
拍她肩膀的手瞬间被抓住,差点把没站稳的他拽倒了。
“孔令麒,你终于出现了……”
“是我……姐,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你跑哪去了,一天不见人,我都怕你出事了……”
“没去哪,我就……姐?你这是……”
他定睛打量着跟前的她,然而她自始至终没睁眼看过自己,只是倚着柱子在喃喃自语。
“回来就好,你还有哪不舒服,告诉我,我保证听,我不会再让小东西受委屈了……”
两颗沉重的泪珠坠落在她紧拉着他胳膊的指缝间,然而她依然没有知觉。
被风刮得有点凉的指节轻轻试了下她额头的温度,俩人霎时同步弹开,不知道是两个极端的温差冻到了她,还是燎着了他。
“姐,马上跟我走……”
神志不清的她居然耍起了赖皮,松开他抓着栏杆不放。
“别碰我,我要等我弟弟回来……”
哭笑不得的他匆匆把地上的提包塞入背囊挎在胸前,一边掰着她的手指,一边凑到耳旁劝说。
“姐,听话,弟弟已经来了……”
连哄带骗好不容易让她撒了手,结果发软的双腿没撑住,险些被她扑倒在地。
遭到抵着肠胃的背包和肩上的重量共同挤压的他,差点把还没消化的食物吐出来。
酒醒了大半的脑中不断警告着:
别倒,不能倒,她是因为你病的,你得像个男人一样负责到底!
颤抖的膝盖终于直起,双手在背后拼命找到合适的地方托住她,然而还没迈出第一步已经喘不过气。
突然站立的眼前金星乱飞,周围霎时都变成了黑白交织的眩晕空间。
绕过脖子的两条手臂把他乱成一锅粥的意识及时唤回,紧接着是蹭在耳畔的碎发和撩入心底的低吟。
“小东西,我冷……”
这鬼魅一般的语调,顷刻间让他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本来已经褪去的酒劲,又翻腾起了热血的亢奋。
他顾不上许多,驮着她埋头使劲往前冲去。
风依旧刮个不停,把她的长发都扒拉成了金毛狮王,下意识挣扎着缩进他背后。
走到一个避风处,他实在累得不行了,把她放下后将帽子给她戴过去,脱掉大衣罩在她身上,摸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上气不接下气地命令道:
“还是我,对……等下给你发个定位,给你钥匙过来帮我找一下车……”
简单擦了一把头上的汗,他重新背起地上的她,踩着棉花般的步伐继续努力前进。
后面的事她就不太记得了,半梦半醒中只听见了两个嗡嗡响在脑海里的声音在对话。
“兄弟,你这是上哪捡到的一个美女?告诉我,我也去试试……”
“去你大爷的,这是我媳妇!”
“你媳妇?不像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赶紧开车,送我们去医院!”
烧得头昏脑涨的她注意力时有时无,躺在病床上还紧紧握着他冻红的手。
当医生把冰凉的听诊器探入她略显紊乱的心口时,明明已经瘫成半熟烤鱼的她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玩命蹦起朝他怀里钻。
这史无前例的行为别说是医生,连他都傻眼了。
但是有病不能不治,他也只能想方设法搜索出一切用得上的好话,哄着她一点点平静下来接受检查。
准备打针吊水时,他搂着伏在肩头的她如坐针毡,仿佛接下来要挨扎的是自己。
医生在旁边端盘拆包的动静,在他看来更像是刑讯室里的磨刀擦枪。
感受到胸前急促的呼吸,他犹豫了很久,还是和医生开了口。
“医生,尽量轻点,她精神紧张了一天,别弄疼了……”
“可以。”
看着闪过寒光的针头逼近她轮廓突起的手背,向来不惧利器的他也没胆直视了,赶紧揽住她的臂弯提前准备好。
一阵痛感从她触到电门般缩回未果的手中迅速传至他的全身,被她突然咬下的肩膀抖得比前面吹冷风时还要剧烈。
“姐……你……算了,你随意吧……”
固定好手上一切的医生,想帮忙卸下浑身僵直的她,却没有成功。
“医生,别动她了,让她自己缓一下,我来照顾就行……”
“她这精神状态怎么紧张成这样?是不是受刺激了?”
“是有点,原因都是出在我身上,后面交给我就好了……”
“不能大意,如果一直没有缓和要赶紧采取措施,不然可能会造成神经方面的损伤……”
“这个我知道,谢谢您关心……”
医生走后,他一手轻压着她扎针的手腕,一手抚过她垂落的长发,忍住肩上的闷痛柔声耳语。
“别怕,放松点,小东西已经回来了,就在你身边……”
脱离幻觉状态的她也累了,无力滑落的身子在他的保护下慢慢躺回了枕头上。
给她盖好被子,才后知后觉被咬的地方火辣辣地疼,稍微一动如同灼烧一样。
尽管冬天穿得厚,可完全无意识的她并没有嘴下留情,两排半清晰的牙印早已在皮肉上刻下了戳记。
替脸色苍白昏睡的她梳理了散乱的头发,一直精神绷紧的他也感到一股强烈的倦意袭来,勉强坚持着调暗屋里的灯光,之后便一头栽倒床边合上了酸涩的眼皮。
这些过程她当然大部分都是蒙在鼓里,只能基本明白是他误打误撞找到了自己,并送到了医院。
至于他去了哪、为什么喝酒,也要等到他醒来才会揭晓答案了。
口中干渴的她很想喝水,但是床头柜上的杯子有一定的距离,她够不着,便将身子挪过去继续尝试。
高烧未退的手指灵活性下降了不少,加上头晕眼花,一只杯子被她的指尖触翻滚落在地。
玻璃碎裂的巨大噪音惊得她一身冷汗,而原本伏案酣睡的他也倏然吓醒,猛地从位置上弹起跌到地板上,捂着伤痛的肩膀连连后退。
她一脸茫然地望着目光盛满惶恐的他,乏力的身体已经支持不起,脱水的嘴唇蠕动着,却只能在喉咙深处发出蚊子声大小的呼唤:
“孔令麒……”
那一刻,他眼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汩汩泪泉,顺着脸颊汹涌倾泻而下。
“孔令麒,你怎么了?有没有被碎片伤到?”
见他按着肩膀面露难色,担心的程蔓想近距离看看这个已经丢了一天的小东西,可是病得绵软的身体根本支撑不住。
伸出被子外的手被他握起轻轻搁回,重新倒了一杯温水。
“姐,想喝水可以叫我的……”
他慢慢把她冒汗的背托起塞好枕头,再把水小心喂到她干涸的唇边。
发现他左边的胳膊一直垂着,她拼命忍着不适问道:
“你左手怎么了?”
“没事,自己在外面撞了一下……”
她还想问什么,他却在试过额头温度后先开了口。
“姐,你还没退烧,先休息吧,明天再说好吗?”
被一肚子问题憋得更难受的她哪里躺得下来,盯着也在一旁灌水的他挤出了一句话。
“先告诉我你今天去哪了?”
“墓园……”
她愣了,这个地方咋就给忽略了呢?
吞下感冒药的他随口应了一声。
“先睡吧,你都跑一天了……”
“你不准再跑了!”
正收拾残局衣角突然被抓住的他身心一颤,转头看到了她泛红的眼眶。
“我不跑,从找到你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打算离开了……”
见他鼻下又挂上了清水,刚想给他抹去,他抢在前面自己用纸巾先蹭掉了。
两个满眼疲倦但逐渐安心的笑脸互相凝视着,相继在彼此的抽泣声中缓缓睡着了。
(未完待续)